《人民的名义》不仅是一部现象级的反腐剧,更是一座流动的古典文学宝库,剧中人物在关键情节处信手拈来的诗词,绝非简单的台词点缀,而是刻画人物心理、预示剧情走向、深化主题内涵的精妙之笔,理解这些诗歌,就如同掌握了开启角色内心世界的钥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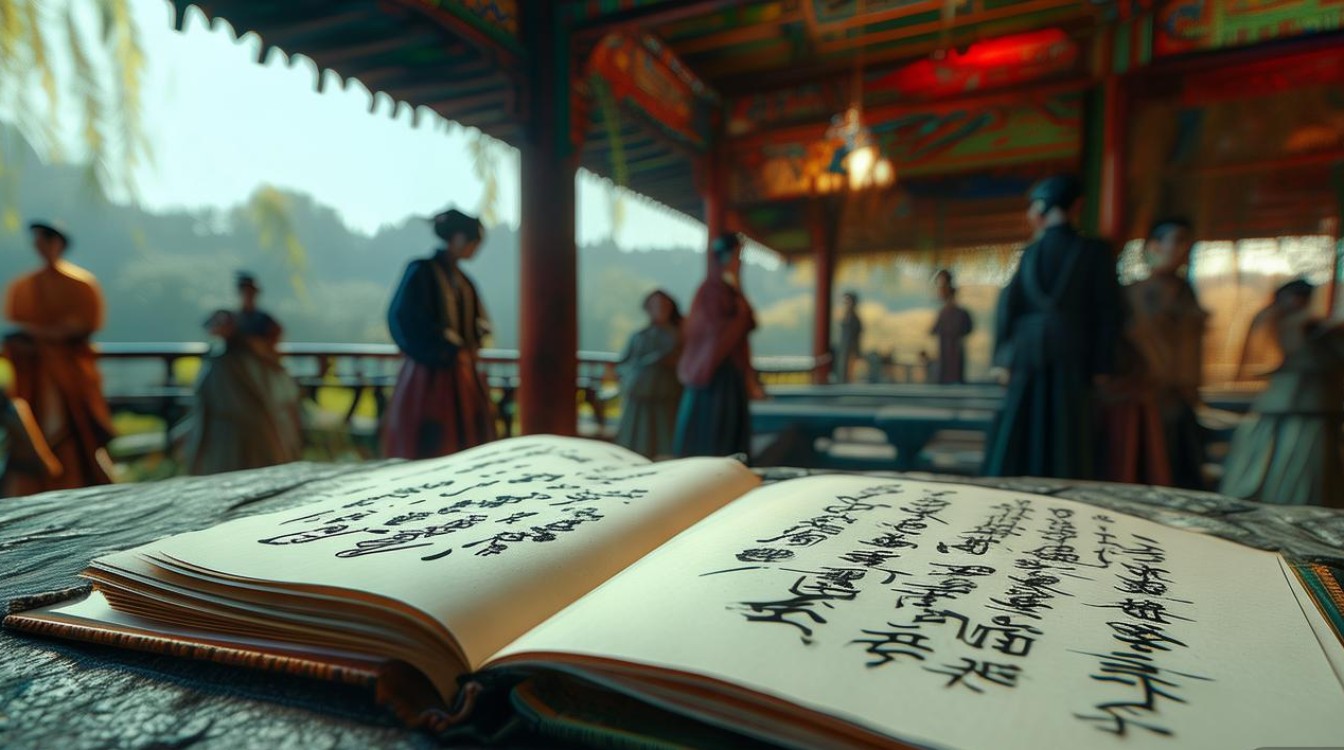
“侯亮平”与“沙瑞金”的志向宣言:古典诗词中的气节与担当
剧中正面角色的诗歌引用,往往直抒胸臆,彰显其理想与操守。
主角侯亮平在剧中多次展现出对古典文学的热爱,其形象与诗歌所承载的正气相辅相成,而省委书记沙瑞金在初次主持省委会议时,引用于谦的《入京》:
“绢帕蘑菇与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,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
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于谦在明宣宗时期,由山西巡抚任上回京,面对当时官场盛行的贿赂之风,他选择不带一物,只凭两袖清风入朝,沙瑞金在此刻引用此诗,其用意极为深刻,这是他个人廉洁自律的宣言,向全省干部表明自己的立场;它是对在场所有官员的一次无声却有力的警示,为后续的反腐风暴奠定了基调,这种“用典”手法,将历史人物的风骨与当代政治生态联系起来,赋予了剧情深厚的历史纵深感。
“高育良”的权谋面具:诗词作为复杂人性的注脚
如果说沙瑞金的诗歌引用是“明志”,那么高育良的诗歌运用则充满了“伪装”与“矛盾”,这也是全剧最具张力的部分。
高育良这位曾经的法学教授,深谙以文化装饰权术,他书房中挂着的郑板桥《竹石》名句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”,本意是歌颂竹子的坚韧不屈,但在他这里,却异化为其在政治漩涡中稳固地位、绝不退让的内心写照,这种对经典诗句的“挪用”,恰恰暴露了他性格中固执乃至顽固的一面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与高小凤之间关于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明史的讨论,其中必然涉及大量古典文化元素,他试图营造一种超脱于俗世权力的文人形象,用风花雪月来掩盖其真实的欲望和抉择,这种将诗词文化作为“保护色”的使用方法,使得高育良这个人物显得格外立体与复杂,他并非不懂诗之美,而是将诗之魂屈从于了个人的私欲之下。
“祁同伟”的悲情绝唱:命运与诗歌的互文
祁同伟的诗歌引用,是全剧最具悲剧色彩和感染力的部分,他饮弹自尽前,在孤鹰岭低声吟诵的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片段,堪称其命运的终极注脚。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这两句诗的本意是文天祥被俘后,表达为国捐躯、青史留名的赤胆忠心,在祁同伟的语境下,这却是一种极具反讽和悲怆的误用,他的“丹心”早已在一次次交易与堕落中蒙尘,他最终追求的并非照耀史册,而是一种扭曲的、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终结,这首诗在此处的“使用方法”,是一种“借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块垒”,他借用了英雄的诗句,来为自己不光彩的一生画上句号,这种强烈的反差,极大地增强了人物的悲剧性,也让观众在憎恶其罪行之余,生出几分对命运弄人的唏嘘。
这种创作手法,通过诗歌与人物命运的强烈“互文”,即文本与现实相互映照,甚至形成对立,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,让角色的形象在落幕一刻达到了顶峰。
诗词在当代叙事中的生命力
《人民的名义》对古典诗词的成功运用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,它告诉我们,古典诗词并非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依然活跃在我们语言和思维中的鲜活细胞。
- 塑造人物:诗歌可以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人物的文化修养、即时心境乃至隐藏的人格。
- 推动剧情:关键诗句的出现,往往是情节转折或深化的信号。
- 深化主题:通过诗歌,可以将个体的故事与民族的文化记忆、历史中的永恒命题连接起来,提升作品的格局。
对于创作者而言,学习这种手法,不仅仅是积累几句诗词,更重要的是理解其精神内核与适用语境,生搬硬套只会显得突兀,唯有像《人民的名义》这样,让诗词与人物的命运、情感血肉交融,才能真正让古典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从沙瑞金的明志,到高育良的伪装,再到祁同伟的悲鸣,诗歌在剧中扮演了多重的、复杂的角色,它让我们看到,同样一句诗词,在不同的人口中、在不同的情境下,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味,这或许正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——它们历经千年沉淀,早已准备好为各种人生境遇提供最精炼、也最深刻的注解,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,多一分对古典文学的了解,也便多了一分理解世界、洞察人性的视角。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