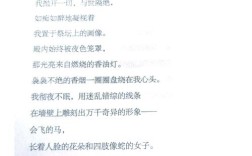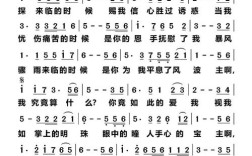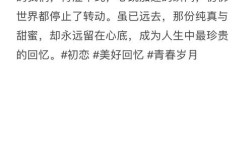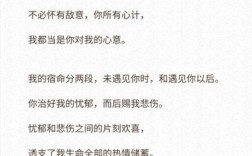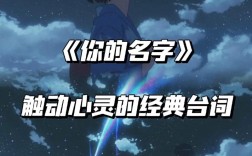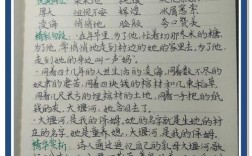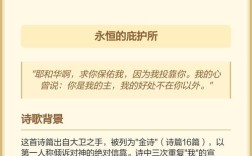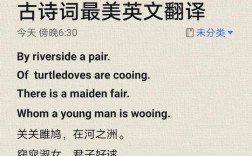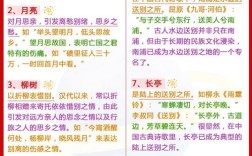诗歌,是语言凝练而成的露珠,折射着人类情感的万千光华,它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,更是一种预感的艺术——在第一个字落下之前,某种情绪、意象或哲思的微光已然在创作者心中闪烁,最终通过特定的形式与技巧,凝固成永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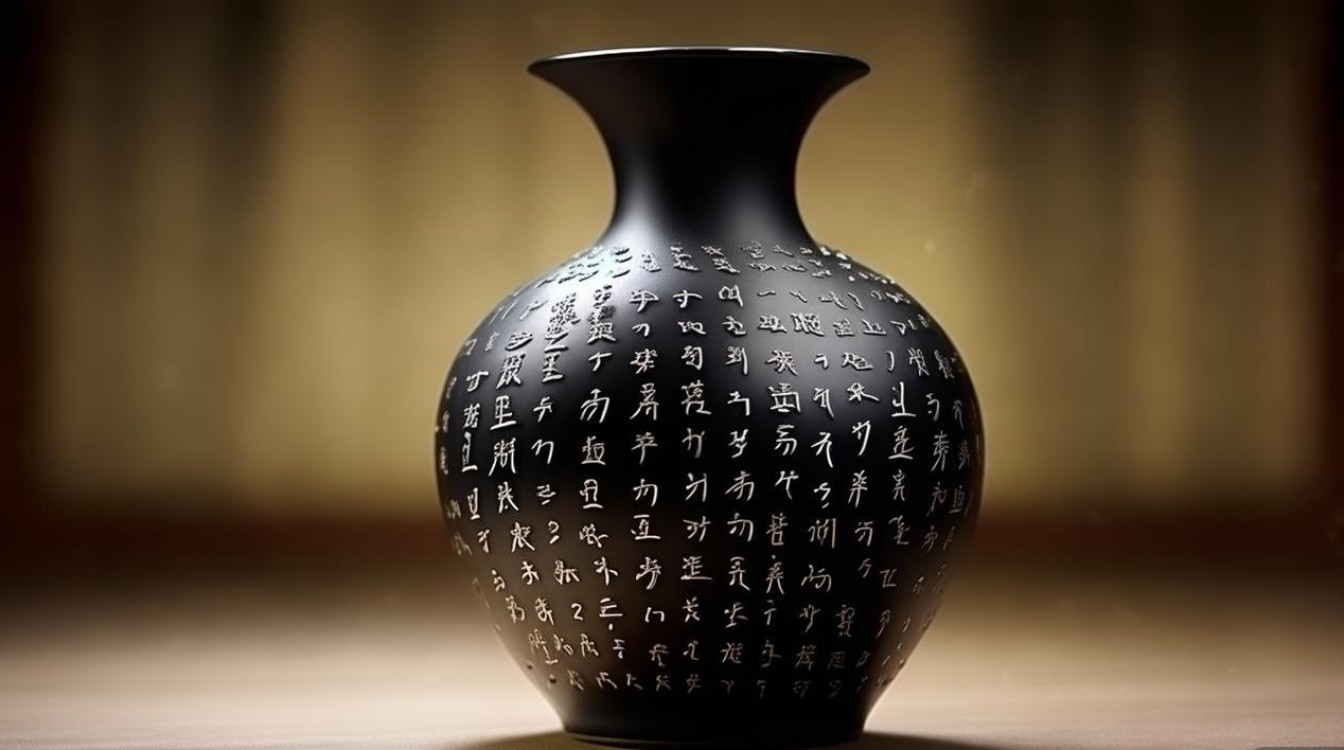
源流与脉动:诗歌的出处与演变
诗歌的起源,几乎与人类语言的诞生同步,最早的诗歌并非书写于纸上,而是回荡在口耳之间,中国的《诗经》便是明证,其中的“国风”多是采诗官从民间收集、整理的歌谣,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的吟唱,是先民劳动、爱情与生活的直接写照,它们没有明确的单一作者,是集体情感与智慧的结晶。
与之相映成趣的,是西方文学的源头——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与《奥德赛》,这些宏大的叙事诗最初也是由行吟诗人口头传唱,歌颂英雄的业绩与神的意旨,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诗歌都始于一种公共的、仪式性的表达,是群体记忆与文化的载体。
随着文明的发展,个人创作开始登上舞台,从屈原的《离骚》,以瑰丽的想象与香草美人的意象抒发政治理想与身世之悲,到李白的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诗歌成为个体生命意志的强烈喷薄,词这一体裁的兴起,如柳永的“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”,更是说明了诗歌与音乐、与市井生活的紧密联系,其传播依赖于特定的乐曲和场合。
灵魂的刻印:作者与创作背景的深度交织
真正理解一首诗,必须尝试触摸其作者的灵魂,并走入孕育它的那个时代,创作背景是解锁诗歌深层意蕴的钥匙。
杜甫被誉为“诗圣”,其作品被称为“诗史”,若不了解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巨大社会动荡,便难以深切体会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中那沉郁顿挫的家国之痛,他的诗歌,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悲剧紧密交织的产物。
同样,现代诗中,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广为传颂,诗中描绘的温暖明亮的愿景,与他最终选择的悲剧结局形成了强烈反差,若知晓诗人处于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的精神困境中,便能感知到这祝福并非单纯的欢欣,而是蕴含着复杂的绝望与决绝,是对尘世最后的、深情的告别。
阅读诗歌,不能将文本与它的创造者割裂,诗人的生平经历、思想情感、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,共同构成了诗歌的“磁场”,影响着每一个字的重量与色彩。
意境的营造:诗歌的核心使用手法
诗歌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体,在于其高度依赖一系列独特的表现手法来营造意境、传递美感。
- 意象:这是诗歌建筑的基石,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,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,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连续叠加的意象直接构建出一幅苍凉萧瑟的秋日图景,旅人的愁思不言自明。
- 韵律与节奏:诗歌具有音乐性,古典诗词的平仄、对仗、押韵,现代诗歌的内在节奏与分行,都服务于情感的起伏,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”,回环的语调和轻柔的节奏,完美复现了那份不忍惊扰的依恋与惆怅。
- 象征与隐喻:这是诗歌通往深邃的桥梁,诗人往往不直接言说,而是借助象征物来暗示,闻一多的《死水》以“一沟绝望的死水”象征当时沉闷衰败的旧中国,表达了渴望变革的强烈愿望,隐喻则如“生命是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蚤子”(张爱玲),通过奇妙的联想,揭示出事物矛盾的本质。
- 凝练与跳跃:诗歌语言追求以少胜多,言有尽而意无穷,它常常省略连接和过渡,形成意义的跳跃,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,顾城的《一代人》,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,两句之间巨大的时空与逻辑跳跃,浓缩了一代人的命运与追求。
心灵的对话:诗歌的品读与运用方法
对于今天的读者,诗歌并非束之高阁的古董,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甘泉。
品读之法,贵在沉潜。 初次接触,不妨高声诵读,感受其音韵之美,继而细细默读,捕捉字词间的意象与情感,查阅相关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生平,能帮助扫清理解的障碍,最重要的是,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与诗歌建立连接,不必强求“标准答案”,个人的、真诚的感受最为珍贵。
运用之道,在于滋养。 诗歌可以成为个人表达的宝库,在书信、演讲或社交分享中,恰当地引用一句诗词,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,它更是内心修养的伴侣,在浮躁之时,读一首王维的山水诗,能获得片刻的宁静;在困顿之际,苏东坡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能带来豁达的力量,将诗歌内化为一种审美眼光,我们便能从平凡生活中发现更多诗意。
诗歌,是人类预感能力的终极体现,它捕捉那些飘忽的思绪,定格那些易逝的瞬间,将混沌的情感梳理成有序的美丽,它跨越时间的长河,让我们与千年前的灵魂相遇,感知彼此的喜悦与悲伤,在物质日益丰沛的今天,对诗意的追寻,或许正是我们对抗精神匮乏、安顿自我心灵的一条幽径,这份由语言创造的预感,终将在懂得它的心灵中,找到永恒的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