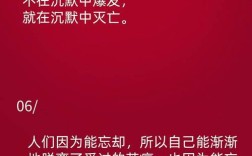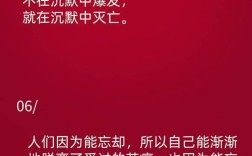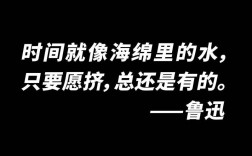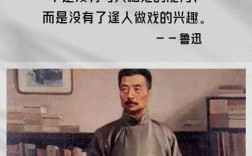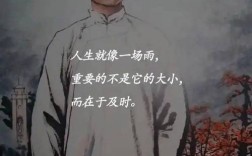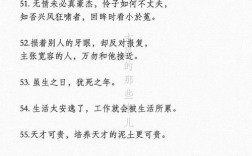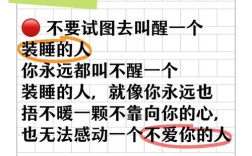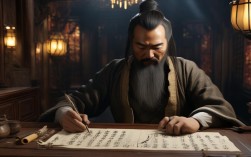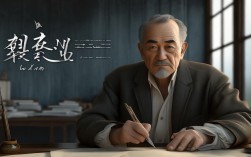鲁迅先生以笔为戈,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,他留下的文字不仅是文学瑰宝,更成为穿透时空的思想利刃,这些警句历经百年依然鲜活,正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核与精湛的语言艺术达成了完美统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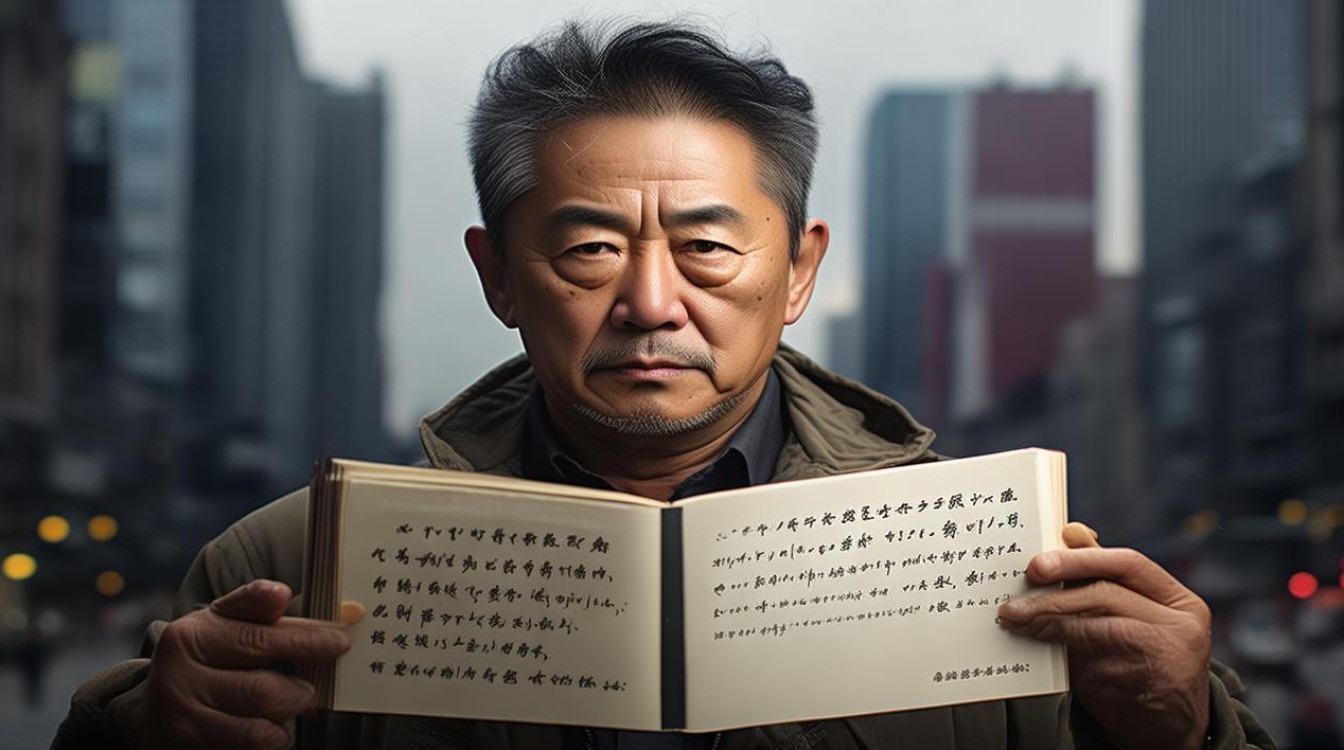
警句溯源:在时代裂痕中迸发的思想火花
要理解鲁迅名言的力量,需回到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场,1918年,《狂人日记》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横空出世,我翻开历史一查……每页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……仔细看了半夜……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”这段文字,不仅揭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,更标志着一种全新批判话语的诞生。
这句名言出自《狂人日记》并非偶然,创作时的中国正处于传统价值崩塌与新生价值未立的断层期,鲁迅透过“狂人”之眼,将几千年的礼教秩序浓缩为“吃人”二字,其震撼力源于对普遍认知的颠覆性重构,这种将复杂社会现象提炼为精准意象的能力,是鲁迅语言艺术的精髓。
《阿Q正传》中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同样如此,创作于1921年的这部中篇小说,塑造了阿Q这一凝聚国民精神痼疾的形象,鲁迅在《再谈保留》中坦言:“我之作此篇,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。”这句话既包含对底层民众的深刻同情,又蕴含对精神胜利法的尖锐批判,这种矛盾统一的情感张力,使八个字承载了远超字面的思想重量。
语言解剖:讥讽艺术的三种武器
鲁迅警句的持久生命力,源自其独特的语言构造艺术,通过解构这些名言的形成机制,我们能掌握思想表达的精密工具。
隐喻转换是鲁迅最擅长的技巧之一。“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”出自《记念刘和珍君》,创作于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这里的“沉默”不仅是状态描写,更被赋予了人格化特征——它成为具有主动性的历史力量,通过将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具有抉择能力的主体,鲁迅使哲学思考获得了情感冲击力。
语境颠覆同样构成鲁迅语言的重要特色。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这句出自《狂人日记》的质问,其力量在于对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进行彻底悬置,在传统观念中,“自古皆然”是行为合理性的重要依据,而鲁迅通过简单反问,就瓦解了这种思维定式的权威性,这种颠覆不依赖复杂论证,而是通过改变认知前提实现思想启蒙。
悖论结构在鲁迅警句中屡见不鲜。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,我觉得充实;我将开口,同时感到空虚”这段出自《野草·题辞》的文字,通过沉默与充实、开口与空虚的矛盾并置,深刻揭示了语言表达与真实体验之间的鸿沟,这种悖论不是逻辑游戏,而是对存在困境的精准捕捉,在矛盾中逼近更深层的真实。
实践应用:让经典言辞焕发当代生命力
理解鲁迅名言的形成机制后,如何在当下社会场景中恰切运用这些思想资源,成为关键问题。
在公共讨论中,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仍具有现实意义,但运用时需注意语境适配——它适用于分析结构性困境中的个体责任问题,而非简单指责弱势群体,例如讨论当代青年发展困境时,既可借此呼吁个体突破精神局限,也要避免忽视社会结构性因素,保持鲁迅原意中的辩证思维。
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这句出自《故乡》的名言,常被用于鼓励创新探索,在技术革新或社会改革的讨论中引用,能赋予行动者以历史建构者的主体地位,但需注意,鲁迅原话强调的是集体实践的创造力量,而非个人英雄主义,这一本质区别决定使用效果。
对于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这句自嘲诗,现今多用于形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,在专业领域,它可诠释为坚守专业标准与服务公众的统一——对错误观念毫不妥协,对公众需求真诚回应,这种态度恰恰契合E-A-T原则中对专业性与权威性的要求。
思想穿透:跨越百年的认知对话
鲁迅警句的价值不仅在于言辞犀利,更在于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——在表象中洞察本质,在常态中发现问题。
这种思维方式对内容创作者尤为重要,鲁迅在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中坦言:“我的取材,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,意思是在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这提示我们,优秀内容不应止于信息传递,更应具备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。
鲁迅名言历经时光淬炼而不褪色,正因为它们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,而是深刻观察与独立思考的结晶,在信息过载的今天,这种基于事实的深刻洞察反而更加珍贵,真正有价值的内容,应当如鲁迅那样,在庞杂现象中提炼本质,用精准语言传递深刻思考。
鲁迅文字的力量最终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勇敢面对与独立思考,在算法支配内容分发的时代,这种思想独立性恰是内容创作者最应珍视的品质,当我们重温“必须敢于正视,这才可望敢想,敢说,敢作,敢当”这段来自《论睁了眼看》的告诫,会发现鲁迅留下的不仅是警句,更是一套完整的认知工具——它教会我们如何看、如何想、如何说,这套工具在今日依然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