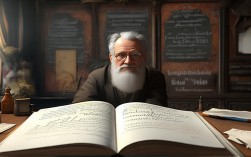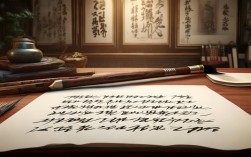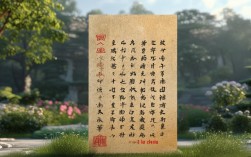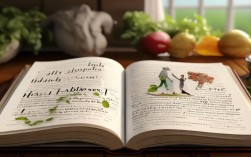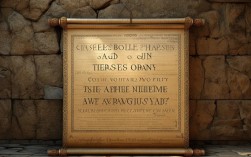关于理想与现实(月亮与六便士)
这是全书最核心的主题,“月亮”象征着崇高的理想、艺术和精神追求;“六便士”则代表着世俗的责任、金钱和安稳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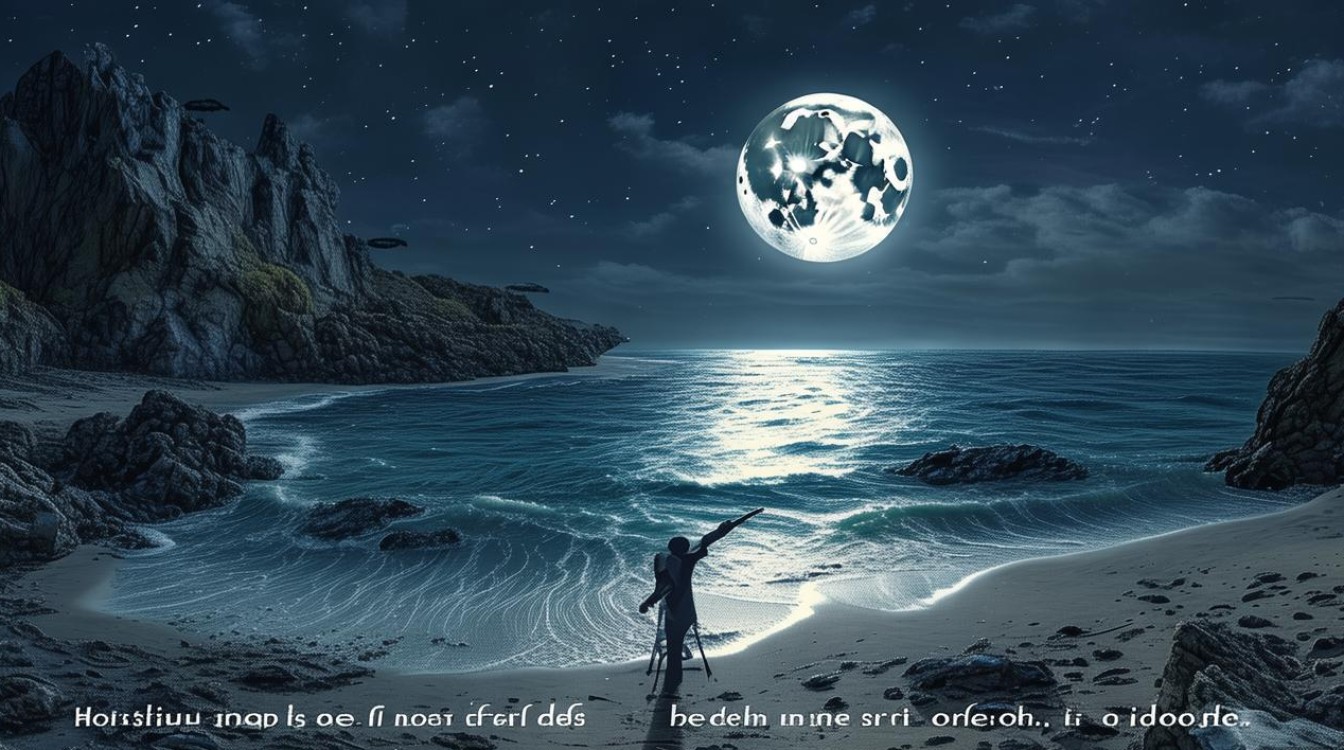
“满地都是六便士,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。”
原文语境: 这是小说书名的来源,也是对主人公查尔斯·思特里克兰德一生最精炼的概括。
解读: 这句话描绘了一个极致的对比,在所有人都为地上散落的六便士(金钱、物质)而忙碌、弯腰捡拾时,思特里克兰德却选择昂起头,凝视着遥不可及的月亮(艺术、理想),它象征着一种对世俗价值观的蔑视和对纯粹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,这个“他”可以是思特里克兰德,也可以是任何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理想而非现实的人。
“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,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,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。”
解读: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思特里克兰德的“异化感”和“无根性”,他并非不爱他的家乡或家人,而是他的灵魂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,他真正的“家乡”是艺术的国度,是一个只有他自己能感知的、抽象的精神世界,这种无处安放的漂泊感,驱动他抛弃一切,去寻找那个真正的“家园”。
“做自己最想做的事,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,淡泊宁静、与世无争,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?与此相反,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,年薪一万镑,娶一位漂亮的妻子,就成功了吗?我想,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,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,对自己有什么要求。”
解读: 这是小说中“我”(作家)与思特里克兰德关于成功与失败定义的对话,它直接挑战了社会普遍的价值观,世俗意义上的成功(高薪、名望、家庭幸福)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毫无价值,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,生命的意义在于内在的满足和精神的实现,而非外界的认可,这迫使读者反思:我们追求的,究竟是自己想要的,还是社会期望我们想要的?
关于艺术与创作
毛姆通过思特里克兰德之口,表达了他对艺术、创作和天才的冷酷看法。
“艺术是情感的客观化。”
解读: 这是思特里克兰德对其艺术创作理念的阐述,他认为,艺术家不应被自己的情感所奴役,而应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,将主观的情感、冲动和体验,转化为一种客观、可供他人审视和评判的艺术作品,这种“抽离”和“客观化”的过程,正是艺术创作(尤其是他追求的原始、质朴的塔希提风格)的关键。
“天才极有可能是疯子,而疯子也极有可能是天才。”
解读: 这句话揭示了思特里克兰德身上那种毁灭性的、非理性的创造力,他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一种偏执和疯狂的地步,这种疯狂让他能抛弃一切道德、情感和社会约束,从而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,毛姆并未美化这种疯狂,而是冷静地指出,伟大的艺术有时与精神上的极端和不稳定相伴相生。
“他就像一个朝圣者一样,怀着一种不可理喻的信念,向着遥远的目标前进,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,也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痛苦,他只听从内心那个魔鬼的驱使。”
解读: 这句话描绘了思特里克兰德创作的驱动力——一种强大、原始、甚至有些邪恶的内在力量,这种力量超越了理智和同情心,是他艺术生命的燃料,他不是一个高尚的英雄,而是一个被命运(或说“魔鬼”)选中的工具,为了艺术可以牺牲一切。
关于人性与道德
小说对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。
“我们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戴着一副假面,而对自己的所知却寥寥无几。”
解读: 这是小说中“我”对人性本质的观察,我们常常通过社会角色和他人期望来塑造自己,戴上了各种各样的“假面”,以至于连自己真实的面目都看不清,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“可怕”,恰恰在于他撕碎了所有人的假面,包括他自己的,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和本性,也因此显得“不正常”。
“卑鄙与伟大是并存的,而且是互为因果的。”
解读: 这句话用来形容思特里克兰德再合适不过,他为了艺术抛弃妻子儿女,冷酷无情,这是“卑鄙”;但他创作出的伟大艺术品,又是“伟大”的,他的伟大建立在对他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之上,他的卑鄙又是他实现伟大的必要条件,毛姆让我们看到,人性并非非黑即白,高尚与丑恶往往交织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“为了使灵魂安宁,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做的事。”
解读: 这句出自书中另一位角色德克·斯特罗伊夫之口,代表了一种与思特里克兰德截然相反的生活哲学,这是一种“中庸之道”,通过日常的责任和妥协来换取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稳定,它讽刺了思特里克兰德那种极端、不妥协的生活方式,也反映了大多数普通人安身立命的智慧。
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的名言之所以经典,在于它们不提供简单的答案,而是提出尖锐的问题,它们迫使读者去思考:
- 我心中的“月亮”是什么?
- 我愿意为它付出多少“六便士”?
- 当理想与世俗冲突时,我该如何选择?
- “成功”的定义究竟是什么?
这些话语穿越了近一个世纪,依然能精准地刺中当代人的内心,引发关于生活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深刻共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