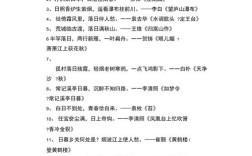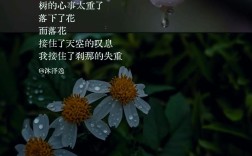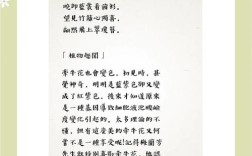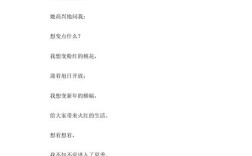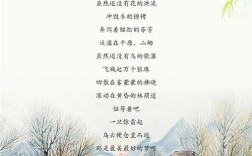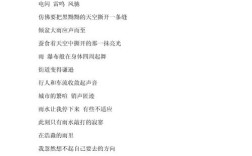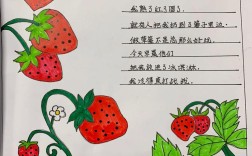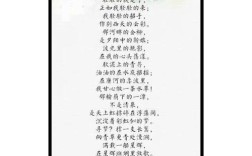现代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和丰富的意象,成为文学创作中独特的存在,这种文体突破传统格律限制,用最精炼的文字承载最深刻的情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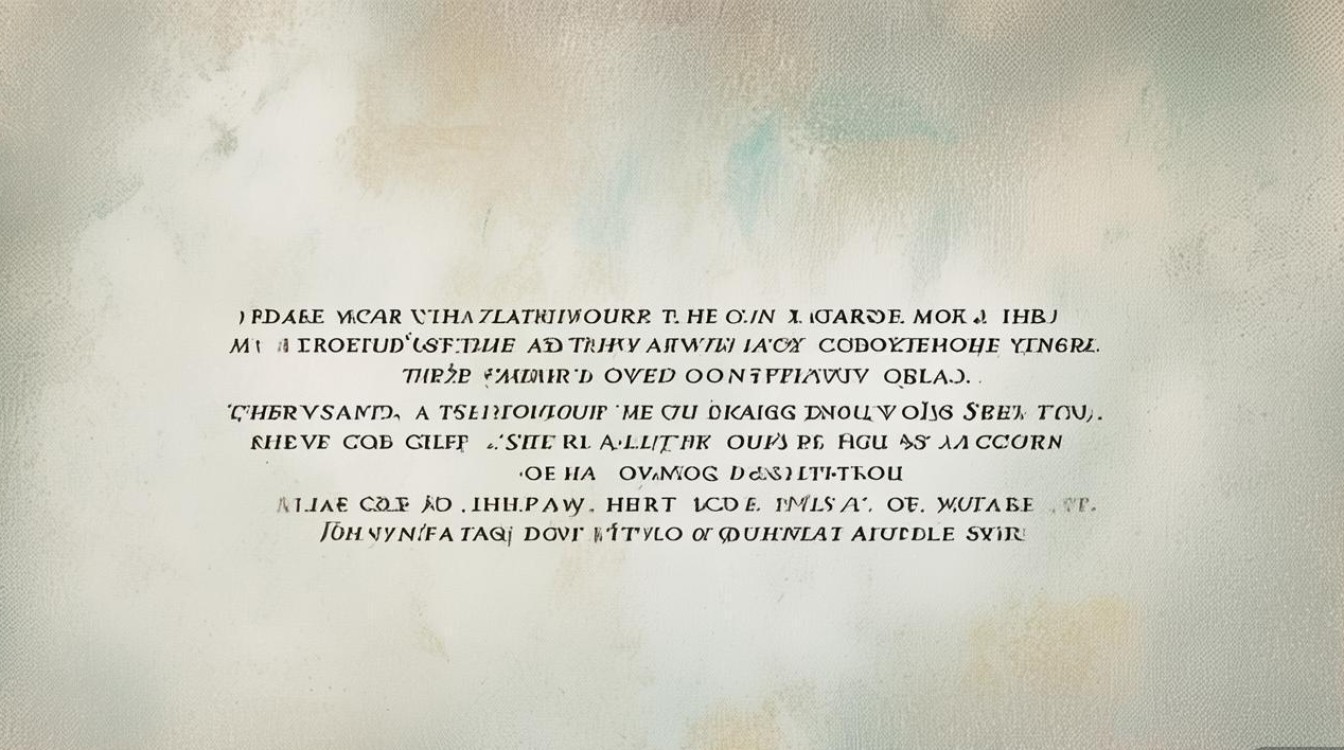
意象:诗歌的呼吸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单元,如同建筑中的砖石,诗人通过意象将抽象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形象,北岛的《回答》中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,通过两组对立意象,构建出对特定时代的深刻反思,这种意象的运用不是简单的比喻,而是将思想情感具象化的过程。
创作现代诗歌时,意象的选择需要遵循内在情感逻辑而非外在形式逻辑,顾城的《一代人》仅用两行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,通过“黑夜”、“黑色的眼睛”、“光明”三个意象的转换,勾勒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历程,这种意象组合产生的张力,远超过单个意象的简单叠加。
语言:打破常规的表达 现代诗歌在语言运用上追求突破常规语法和词汇搭配,创造出新的表达可能,余光中的《乡愁》将抽象情感与具体物象相连:“小时候/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/我在这头/母亲在那头”,通过将“乡愁”与“邮票”、“船票”、“坟墓”、“海峡”并置,语言在这里不再是交流工具,而成为情感的载体。
这种语言创新要求诗人对词语有敏锐的感知力,每个词都承载着声音、意义和形象三重属性,优秀的诗人能同时调动这三重属性,使诗歌在朗读时具有音乐性,在理解时具有多义性,在想象时具有画面感。
节奏:内在的韵律 现代诗歌虽不严格遵循传统格律,但仍保持内在节奏感,这种节奏不是通过平仄或押韵实现,而是通过词语长短、句式变化、重复等手法营造,舒婷的《致橡树》通过排比句式形成强烈节奏感: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/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/根,紧握在地下/叶,相触在云里”,这种节奏源于情感的自然起伏,而非外在形式要求。
把握诗歌节奏需要反复诵读和修改,诗人通常通过调整句式长短、词语位置来控制阅读的停顿与连贯,使诗歌形式与内容达到和谐统一。
结构:情感的轨迹 现代诗歌结构自由,但绝非随意安排,每首诗都有其内在结构,这种结构是诗人情感流动的轨迹,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从“从明天起”的反复咏叹,到最后“我只愿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转折,结构上形成从外向到内向的转换,恰好对应了诗人从世俗幸福到个人坚守的情感变化。
理解诗歌结构需要关注诗句之间的空白,现代诗歌中,未言说的部分往往比言说的部分更重要,这些空白留给读者想象空间,使读者参与诗歌意义的创造。
创作过程:从感受到表达 诗歌创作通常始于某种强烈感受或瞬间印象,诗人捕捉这种感受,寻找合适的意象和语言予以表达,这个过程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,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都可能成为诗歌的素材,关键在于诗人能否从中发现不寻常的意义。
修改是创作的重要环节,初稿往往包含过多解释性或过渡性语句,这些都需要在修改中删减,直到只剩下最核心、最有力的部分,真正的诗歌是去芜存菁后的结晶。
阅读方法:主动参与 阅读现代诗歌需要主动参与,而非被动接受,面对一首诗,不妨先通读全篇,感受整体氛围;再细读每行,品味词语的微妙;最后思考诗歌引发的联想和思考,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可能有不同理解,这正体现了诗歌的丰富性。
多次阅读同一首诗常常会有新的发现,优秀的诗歌经得起反复品读,每次阅读都能带来新的感悟。
现代诗歌的价值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现代诗歌以其简洁和深刻提供了一种对抗语言粗糙化的方式,它提醒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停下脚步,感受语言的精妙和情感深度,诗歌不需要复杂辞藻或艰深理论,真正打动人心的诗歌往往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情感。
诗歌创作是探索语言可能性的过程,也是认识自我、表达自我的途径,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用诗歌记录生活感受,不必拘泥于形式技巧,真诚的表达往往最具力量,在这个强调实用和效率的时代,诗歌守护着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和语言的多样性,这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