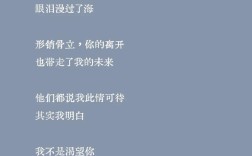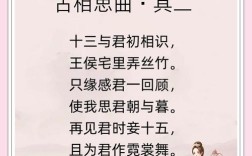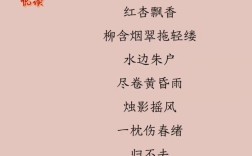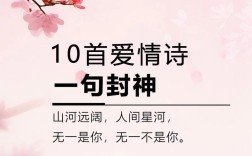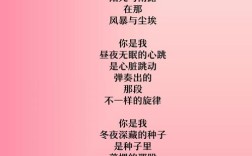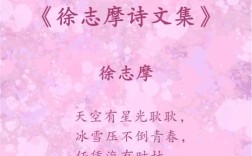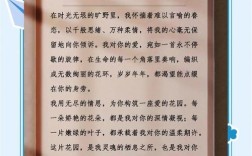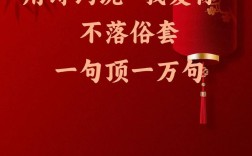诗歌,是语言凝练而成的琥珀,封存着人类最精微的情感与最深邃的思考,它跨越时空,将千年前的心跳与此刻的我们紧密相连,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由文字构筑的“爱恋”之境,探寻诗歌的内在肌理与永恒魅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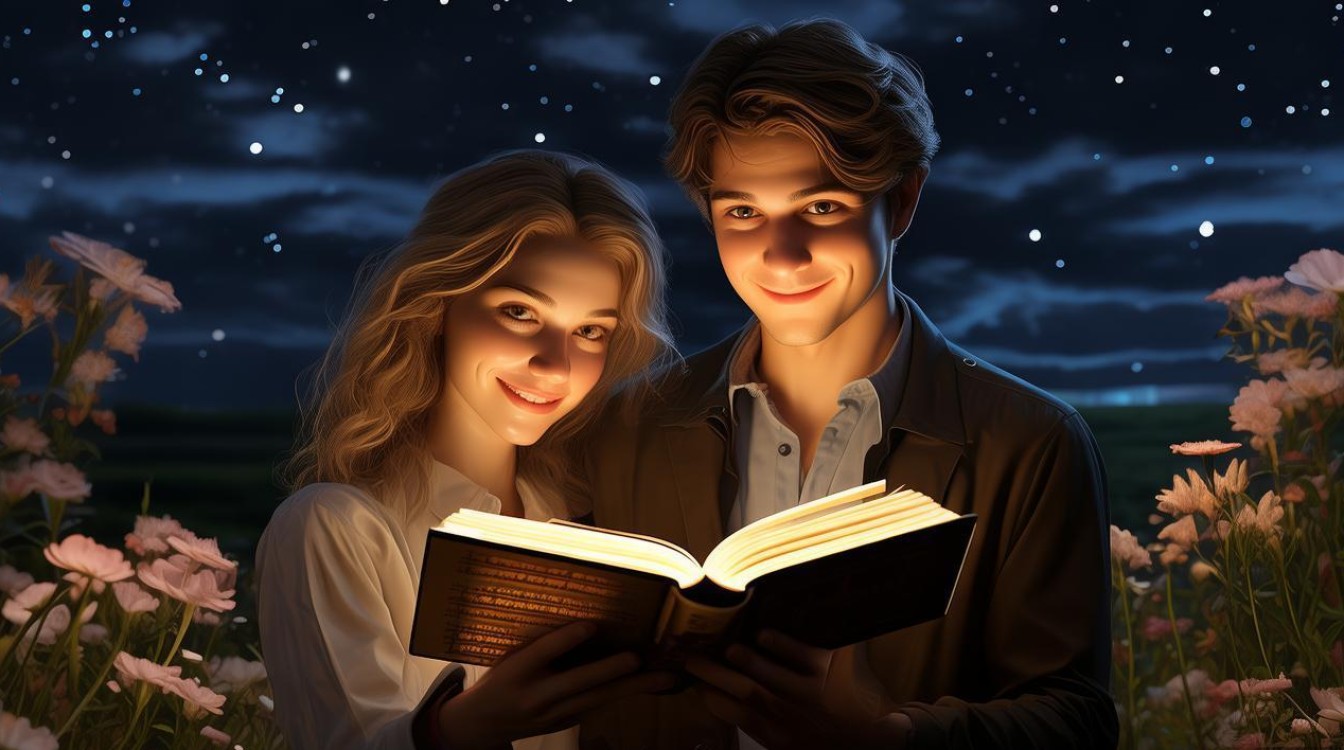
溯源:诗歌的源流与经典
诗歌的起源与人类文明同步,它是先民于劳动中的号子,是祭祀时的祷词,是心中情愫最原始的抒发,中国的诗歌长河,源远流长,从集体创作的《诗经》——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的质朴起兴,到屈原《楚辞》——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瑰丽想象与个人咏叹,奠定了诗歌的两大传统。
至唐代,诗歌步入黄金时代,李白以其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磅礴气势,展现了盛唐的豪迈与不羁,其诗作想象奇绝,语言奔放,是浪漫主义的高峰,杜甫则用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沉痛笔触,记录时代的疮痍与民生的疾苦,其诗风沉郁顿挫,被尊为“诗史”,代表了现实主义的深度。
宋代文人另辟蹊径,将情感与哲思融入词这一长短句形式中,苏轼一曲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开豪放词风,旷达超逸;李清照则于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的吟哦中,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婉约词风推向极致,这些作品,无一不是其时代精神与个人生命体验的交响。
探微:创作背景的密码
真正读懂一首诗,往往需要解开其创作背景的密码,这背景是诗歌生长的土壤,包含着时代的风云、作者的生平与具体的心境。
南唐后主李煜的词,亡国前是“划袜步香阶,手提金缕鞋”的宫廷艳情,亡国后则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深哀巨痛,不了解其从一国之君到阶下之囚的巨变,便难以体会其词中血泪的分量,同样,理解了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摧毁性打击,才能深切感受杜甫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中所蕴含的黍离之悲。
背景知识如同一把钥匙,能为我们打开通往诗歌内核的通道,让静止的文字重新焕发出时代的风雷与作者温热的呼吸。
致用: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活化
诗歌并非博物馆中的古董,它可以且应当活在我们的日常之中,其使用方法,远不止于背诵与鉴赏。
诗歌是情感的精准容器,当我们陷入爱恋,一句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或许比千言万语更能传达执著;当我们思念远方之人,“此时相望不相闻,愿逐月华流照君”便道尽了无声的牵挂,在社交场合,恰当地引用诗句,能瞬间提升交流的质感,彰显个人的文化底蕴。
诗歌是绝佳的创作素材与灵感源泉,现代广告文案、歌曲歌词、乃至品牌故事的讲述,都常从古典诗词中汲取意象与意境,将诗歌的意境融入摄影构图,或用书法抄录一首心仪的作品,都是让诗歌参与生活、滋养性情的雅事。
析艺:诗歌的艺术手法鉴赏
诗歌的魅力,极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独特的艺术手法,这些手法是诗人锻造情感的砧锤。
- 意象与意境:意象是融入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,如“月亮”代表思念,“杨柳”象征离别,多个意象组合,便营造出意境——一个可供读者沉浸和回味的艺术空间,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,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一系列意象的铺陈,共同渲染出天涯游子孤寂凄凉的意境。
- 韵律与节奏:诗歌天生具有音乐性,平仄的交替、韵脚的呼应,构成了内在的韵律美感,无论是古体诗的严谨格律,还是现代诗的自由节奏,其声音的流动都与情感的表达相辅相成。
- 修辞的妙用:比喻能让抽象变得具体(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);拟人能赋予万物情感(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);用典则能在有限的字句中,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,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张力。
掌握这些手法,如同获得了一张详尽的“寻宝图”,能引导我们更深入地领略诗歌艺术的精妙所在。
诗歌,这盏由历代智者与诗人点燃的明灯,照亮着我们共同的情感世界,它告诉我们,关于爱恋、关于生命、关于世界的困惑与洞察,古已有之,我们并不孤独,在节奏日益匆忙的今天,或许我们更应当时常驻足,品读一首诗,让千年的智慧洗去心尘,让古老而鲜活的情感润泽生命,这不仅是与传统的对话,更是一次对自我内心的深刻观照与滋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