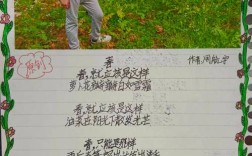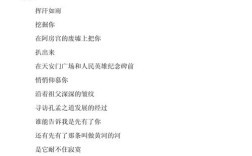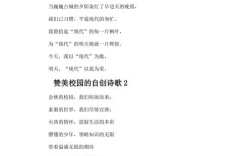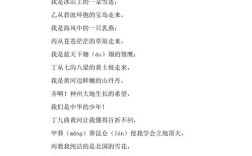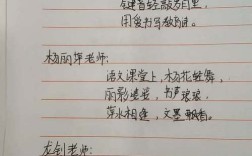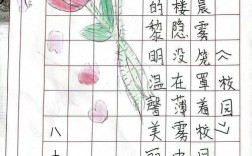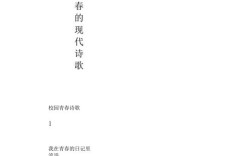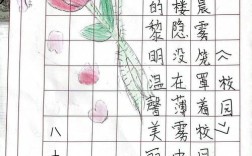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,校园诗歌更是青春记忆里最清澈的泉眼,当青涩的情愫与文字相遇,便凝结成值得一生珍藏的珠玉,要真正读懂一首校园诗歌,需要从多个维度进入它的世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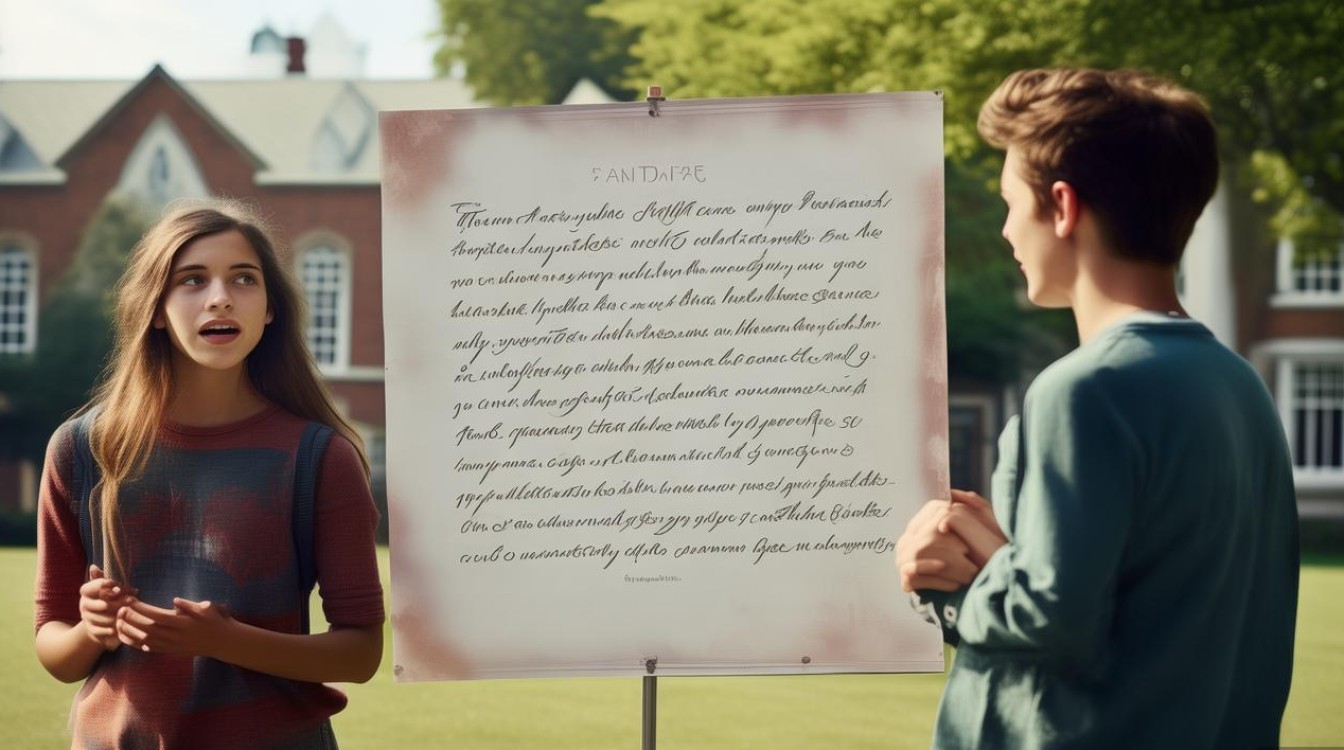
溯源:从字句间探寻诗歌的根系
每首诗歌都有其独特的生长环境,了解诗歌的出处与作者生平,如同获得一把打开理解之门的钥匙。
以经典校园诗歌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为例,这首诗创作于1989年,距离海子去世仅两个月,了解这一点,我们便能从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”这明媚的语句中,读出诗人对理想生活的深切渴望与现实的复杂况味,海子作为北大校友,他的创作与校园经历密不可分,诗中纯净的意象与炽热的情感,正是校园诗歌特质的集中体现。
同样,席慕容的《青春》之所以能在几代学子中传唱,与她的师范教育背景及对青春主题的执着书写直接相关,她在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求学经历,使得诗歌兼具文字的韵律与画面的美感。
解码:在时代坐标中理解诗意
创作背景是诗歌的时空坐标,它决定了诗歌的情感基调和思想内涵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普遍充满理想主义光芒,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相契合;而九十年代的诗歌则更关注个体感受与日常生活细节。
顾城的《一代人》仅有两句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这首诗写于1979年,了解其创作于文革结束后的历史背景,我们才能深刻体会这短短话语中蕴含的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历程——从迷茫到觉醒,从压抑到追求。
理解创作背景,并非要将诗歌简化为时代标签,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诗人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,完成个人体验与普遍情感的融合。
活化:让诗歌融入当下生活
校园诗歌不应只是文学教材中的标本,而应是可感、可用的生活养分,这里介绍几种将诗歌融入日常的方法:
朗诵是最直接的体验方式,通过声音的节奏、停顿、轻重,能激活诗歌内在的音乐性,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尤其适合朗诵,其语言的柔美波动与情感的起伏完全同步。
摘抄是深化记忆的过程,亲手书写能够促进对诗歌结构与字词的细致观察,在摘抄汪国真的《热爱生命》时,读者会自然留意到“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”中递进的逻辑关系。
诗歌还可以作为创意表达的素材,将诗句融入手账、设为签名、改编成歌曲,甚至作为演讲的开场,都是让诗歌焕发新生命的方式,冰心《繁星·春水》中的短诗,因其简洁隽永,特别适合这类创造性使用。
细读:掌握解析诗歌的艺术
深入欣赏诗歌需要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:
意象解读是核心环节,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单位,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,读郑愁予的《错误》,需注意“江南”“莲花”“东风”“柳絮”“青石的街道”等意象共同营造的婉约氛围,理解“美丽的错误”这一矛盾修辞表达的复杂心境。
韵律分析不可忽视,古典诗词的平仄、对仗、押韵有严格规范,现代诗虽形式自由,但同样讲究内在节奏,分析余光中的《乡愁》,会发现诗中“头”字的重复押韵,以及“小小的”“窄窄的”“矮矮的”“浅浅的”等叠词运用,形成如泣如诉的旋律感。
比较阅读能拓展理解维度,将同一主题的不同诗歌并置阅读,如对比舒婷《致橡树》与裴多菲《我愿意是急流》中的爱情观,能更清晰地把握每首诗的独特价值。
创作:从读到写的自然延伸
在充分阅读积累后,尝试创作是深化对诗歌理解的途径,校园诗歌创作可从这些方面入手:
捕捉真实瞬间,课堂上的走神、食堂里的拥挤、操场上的奔跑、考试前的紧张,这些校园生活的独特场景都是诗歌的优质素材。
建立个人意象系统,从个人经验中提炼专属意象,使表达更具独创性,某个特定的教室座位、校园里一棵有故事的树、晚自习的灯光,都可以成为情感的载体。
注重语言锤炼,诗歌是精炼的艺术,需要反复推敲字句,初稿完成后,通过删减、替换、调整,使每个词都不可替代。
诗歌是时间的容器,封存着特定年纪的欢笑与泪水,在人人追逐实用技能的时代,诗歌似乎缺乏即时效用,但正如无人会问听一首歌、看一场日落有何具体用处,阅读和创作诗歌的价值,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,一种表达情感的途径,一种在实用主义浪潮中保持精神独立的力量。
真正优秀的校园诗歌,能够穿越时光隧道,在多年后依然唤起我们内心的共鸣,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起点,更是心灵成长的见证,当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重温这些诗行,实际上是在与曾经的自己对话,测量这些年来精神跋涉的里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