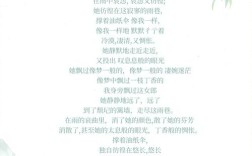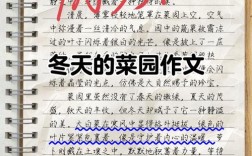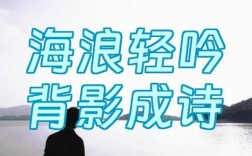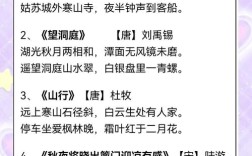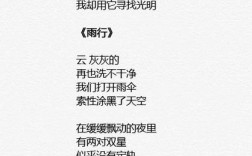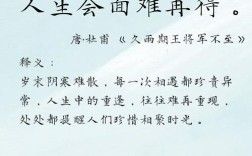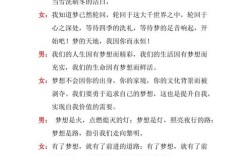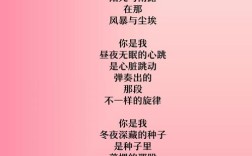黄昏的帘幕落下,夜晚便铺开它无边的稿纸,星辰是标点,月光是分行,无数诗人在此伏案疾书,夜,这一永恒主题,在现代诗歌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面貌——它时而是思想的庇护所,时而是情感的放大镜,时而又成为存在之谜的隐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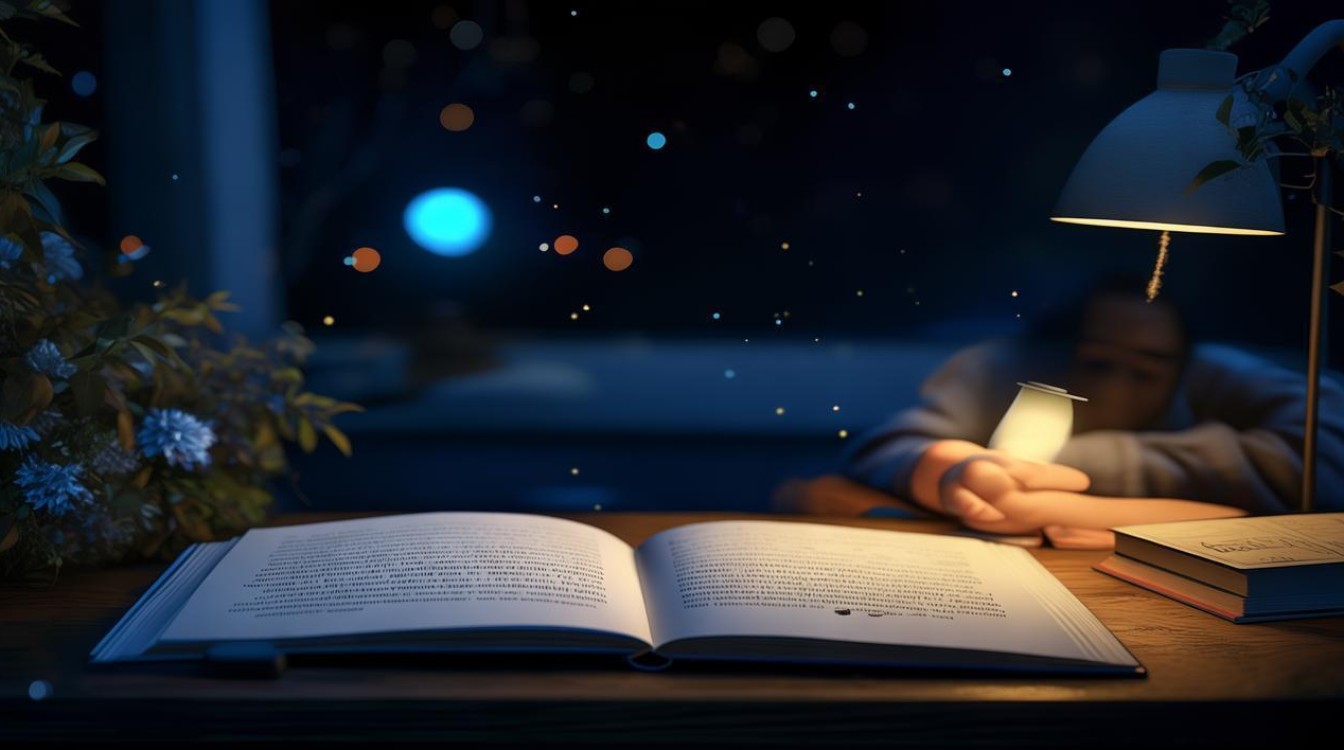
夜色作为创作母题
现代诗中的夜色早已超越“床前明月光”的单一意象,以洛夫《子夜读信》为例:“你的信像一尾鱼游来/读水的温暖/读你额上动人的鳞片/读江河如读一面镜/读镜中你的笑/如读泡沫”,这里,夜不再是背景,而是化为流动的媒介,将私人情感升华为超现实的幻美,诗人利用夜的静谧与神秘,构建起一个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审美空间。
这种转变源于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变化,当白昼被理性与规则统治,夜晚便成为潜意识与直觉的出口,如同翟永明在《女人·独白》中写道:“我,一个狂想,充满深渊的魅力/偶然被你诞生”,夜色在这里成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温床,那些在白日被压抑的声音,在月光下获得了合法的表达权。
意象系统的构建艺术
现代诗人笔下的夜,往往通过独特的意象系统完成,北岛在《午夜歌手》中这样处理:“一首歌/是夜漫出的血/蜘蛛捕获的/星星在网中/结出光芒”,夜被赋予液体的质感,歌声与血液同构,蜘蛛网与星空的并置产生陌生化效果,这种意象嫁接手法,打破了古典诗词中夜意象的程式化表达。
值得注意的是意象的私人化倾向,在张枣的《镜中》,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,夜与悔恨、梅花、南山形成个人化的符号系统,这种写作策略要求读者放弃对夜的先入之见,进入诗人独有的情感逻辑。
声音的韵律实验
现代诗对夜的表现,在声音层面也展现出丰富探索,商禽在《夜》中运用散文诗形式:“夜,墨水似的弥漫,我是一张被写满的纸。”短促的句式模拟了夜的窒息感,语言的留白恰似夜色中的虚无,这种形式创新,让诗歌的声音质地与主题达到高度统一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炼的《诺日朗》:“午夜降临/高原如猛虎/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”,这里采用密集的意象和强烈的节奏,让夜充满原始的生命力,诗人通过控制语速和音调,使语言本身成为夜的交响。
创作技法的具体运用
若要书写属于自己的夜,不妨从这些技法入手:
意象的陌生化处理:避免直接使用“黑暗”“寂静”等陈词,试将夜想象成“未完成的素描”(陈黎语),或“巨大的听觉器官”(痖弦语),通过非常规的比喻,赋予夜新的感知维度。
时空的压缩与延展:如周梦蝶在《菩提树下》所做:“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?/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?”将佛教典故与个人冥思压缩入夜的时空,使瞬间获得永恒的重量。
感官的错位与融合:借鉴蓉子的《晚秋的乡愁》:“桂花蒸/古老的鼎/焚着淡淡的香”,将嗅觉、视觉、温度觉交融,创造出立体的夜之体验。
私人符号的建立:如同海子在《夜晚 亲爱的朋友》中多次使用的“麦地”“月亮”,形成个人化的夜之词典,这种符号系统让诗人的夜区别于他人,具有可辨识的风格印记。
现代性视野下的夜
当代诗歌中的夜,更呈现出多元的面貌,部分诗人将夜与城市经验结合,如颜艾琳在《黑暗温泉》中写道:“纽约的夜/是一块巨大的冰/在摩天楼的杯子里摇晃”,夜成为现代都市的隐喻,反射着物质文明的冷光。
另一些诗人则回归乡土,如陈黎在《夜》中的描绘:“夜是永远清醒的/一亩田,在我们里面/转动它黑暗的光”,这种处理将夜与土地、记忆相连,为现代人的精神漂泊提供锚点。
阅读夜诗的方法
理解现代夜诗,需放弃对“美”的单一期待,许多优秀作品,如夏宇的《野兽派》中“二十世纪的月亮/被疯狗咬了一口”,呈现的是破碎、荒诞的夜景,这种审美体验更接近现代人的真实处境。
同时要注意诗歌中的沉默之处,正如默温所说:“诗歌不是用词语说出的事物,而是词语试图说出的沉默。”夜的诗歌尤其如此,那些未言明的部分,往往承载着更深的意蕴。
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窗口眺望夜色,我们手中的笔或许比古人更自由,却也更加沉重,当城市的霓虹稀释了纯粹的黑暗,当信息的洪流淹没了静默的权利,诗歌中的夜反而显得更为珍贵,它提醒着我们:在所有人造的光明之外,仍存在一种原始的、无法被完全驯服的力量,等待着语言的勘探。
书写夜,最终是为了重新发现那些在白日的喧嚣中失落的自我,每一首关于夜的诗,都是诗人与无限的一次私密对话,也是现代灵魂在技术时代的精神自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