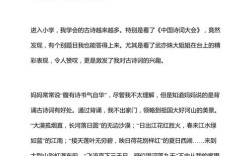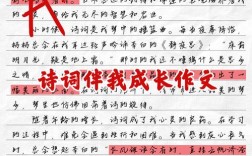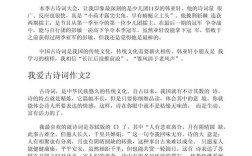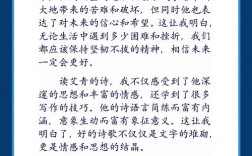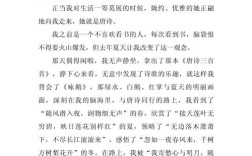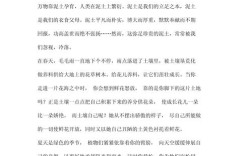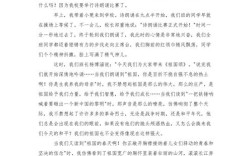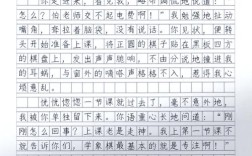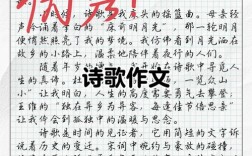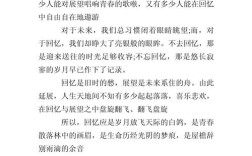每当夜深人静,总有一卷唐诗或半阕宋词在案头与我相伴,最初接触诗歌,是小学时摇头晃脑背诵“床前明月光”,那时只觉得韵律好听,却不知这短短二十字将伴随我一生,随着年岁渐长,我才逐渐明白,诗歌不是束之高阁的文物,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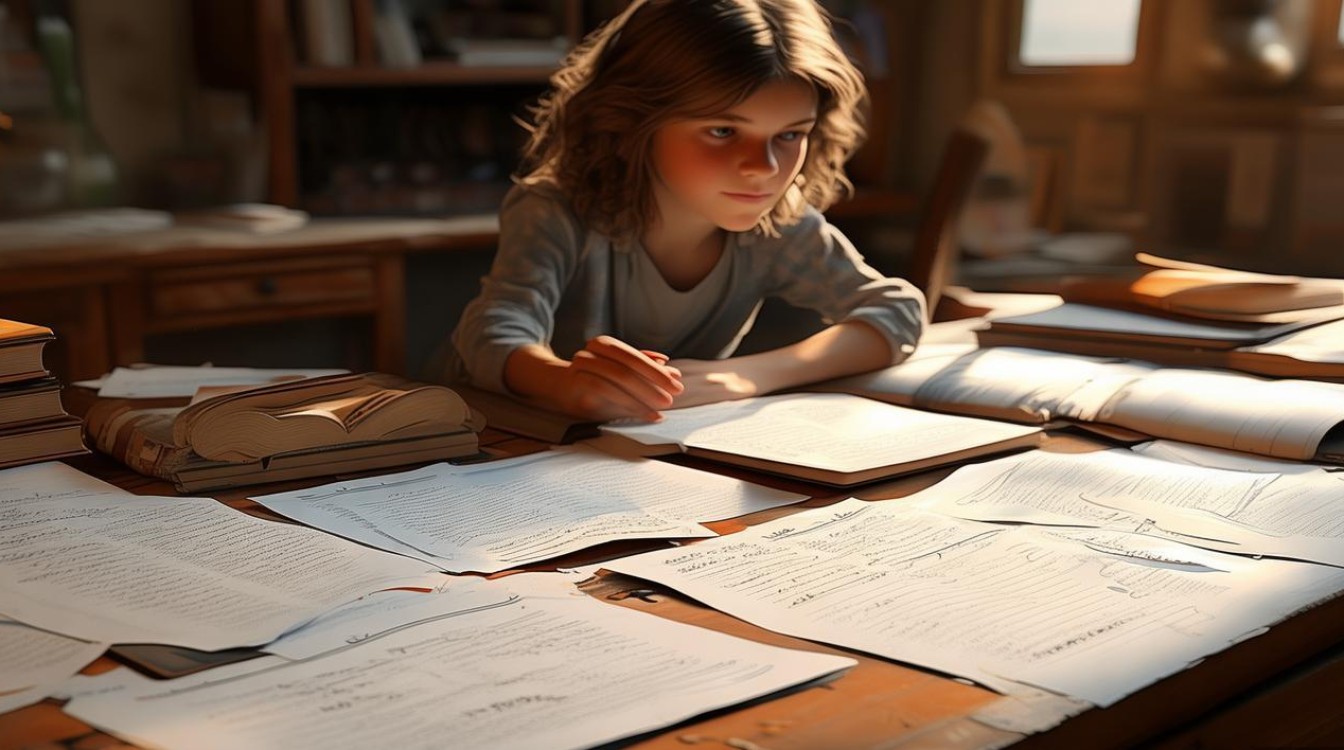
格律:汉字音乐性的极致表达
中国古典诗歌最迷人的特点在于其音乐性,平仄交替如同呼吸,抑扬顿挫间构建出独特的节奏美感,以五言律诗为例,其平仄规律如同精心设计的建筑,每个字的位置都经过千年锤炼。
杜甫《春望》开篇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平仄为“仄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”,这种对称不仅营造了听觉上的和谐,更与诗人对战乱后荒凉景象的沉痛感慨相呼应,理解平仄规律,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诗歌情感密度的变化。
对仗则展现了汉语的对称美学,李商隐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不仅字面工整,意象也相互呼应——春蚕的执着与蜡烛的奉献,共同构筑了爱情的坚贞,学习欣赏对仗,关键在于发现表面工整之下意象的深层关联。
意象:千年文化密码的传承
中国诗歌有一套独特的意象系统,这些意象经过千年沉淀,已成为浓缩的文化符号。
月亮在诗歌中从不只是天体,它承载着乡愁、哲思与人生感慨,李白《月下独酌》中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,月亮成了寂寞中唯一的知己;苏轼《水调歌头》里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,月亮又化作世事无常的象征。
理解这些意象的文化内涵,是打开古典诗歌大门的钥匙,柳条总是与离别相关,源自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;东篱往往暗示隐逸情怀,出自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典故,这些意象如同文化基因,在历代诗人的笔下不断重组、变异,却始终保持核心的象征意义。
创作背景:诗与时代的对话
真正理解一首诗,必须将其放回创作的历史语境中,杜甫被称为“诗史”,正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。
《春望》写于安史之乱期间,长安沦陷,诗人被困城中,明白这一背景,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的痛楚才显得如此真切,花鸟本无情,但在国破家亡的诗人眼中,它们都在为这场灾难悲泣。
李煜后期词作的巨大感染力,同样来自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碰撞,从一国之主到亡国俘虏,《虞美人》中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浩叹,是个人的悲歌,也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挽歌。
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活化
古典诗歌不应只是课本中的知识点,更可以成为现代生活的精神资源。
我在工作中遇到瓶颈时,常会想起陆游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豁达;面对选择时,王安石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的警句提醒我审慎决策,这些千年之前的诗句,依然能照亮现代人的心灵困境。
创作实践是更深层次的传承,不必拘泥于严格的平仄对仗,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瞬间开始:通勤路上阳光穿过树叶的斑驳,深夜加班时窗外孤独的灯火,都可以用简练的文字记录下来,这种训练能培养我们对美的敏感度。
我尝试将现代意象融入传统形式,写过“键盘敲落星三点,屏幕点亮夜五更”,虽不及古人境界,却在古今融合中找到了表达当代生活的新途径。
品读方法:慢下来的艺术
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,读诗需要一种“慢下来”的勇气,我习惯在清晨或深夜,泡一杯清茶,反复吟诵一首诗,起初可能只觉得文字优美,但多读几遍,诗的意境便会逐渐浮现。
王维《山居秋暝》需要静心品味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不只是写景,更传递出诗人放下尘世纷扰后的心境转变,读到最后“随意春芳歇,王孙自可留”,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的灵魂洗礼。
这种阅读体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尤为珍贵,它训练我们暂停匆忙的脚步,重新发现被忽略的生活细节,恢复对美的感知能力。
诗歌于我,已从少年时的课业负担,变成了成年后的精神栖息地,在格律中感受汉语的音乐性,在意象间破译文化密码,在创作背景里理解诗人心路,这些过程让遥远的诗歌变得亲切可触,真正的好诗从来不会过时,它们只是等待合适的时刻,与合适的灵魂重逢,每当生活令人疲惫,我总会想起苏轼那句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——千年前的宽慰,至今依然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