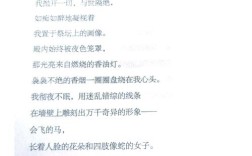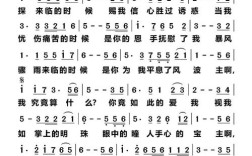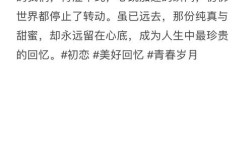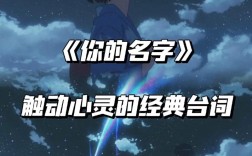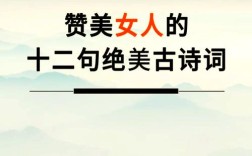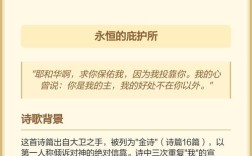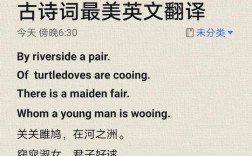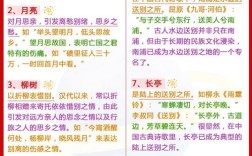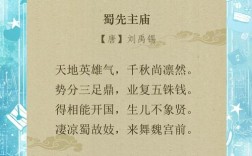(空一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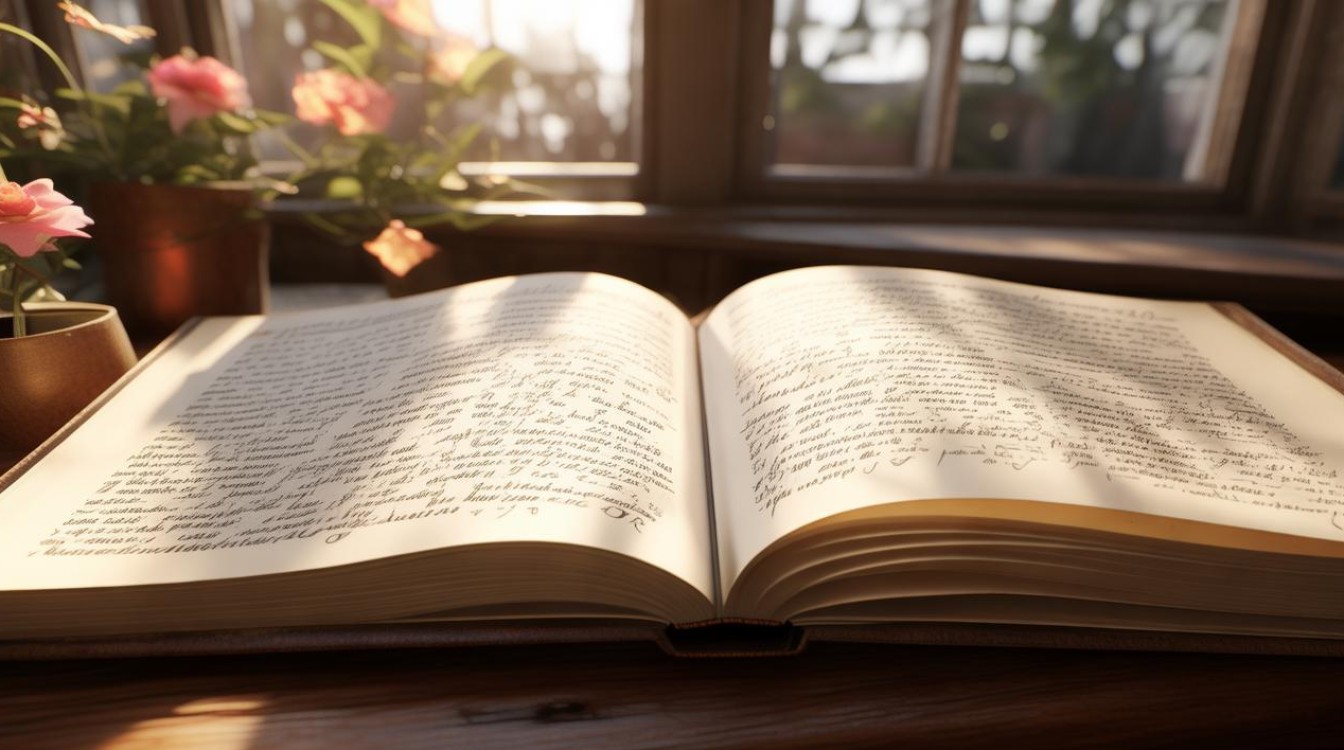
暮色四合,书页间偶然飘落一枚干枯的银杏书签,夹着的是多年前手抄的半阕旧词,墨迹已有些淡,那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却依然清晰,这一瞬的停顿,仿佛时光特意安排的窄门,我们又与诗歌不期而遇,它从未远离,只是静候在生活的某个转角,等待一次心灵的共振。
诗歌,是汉文字最精妙的阵法,它并非高悬于穹顶的冰冷星辰,而是先民“杭育杭育”的劳作号子,是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婉转咏叹,这些古老的歌谣,源自土地、爱情、征战与日常,是生命最质朴的流露,理解一首诗,如同结识一位老友,需知他从何处来,曾历经怎样的风雨。
探寻诗歌的源头,是深入其肌理的第一步,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,若只读其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轻快,便失却了厚度,需知此诗写于他因永王李璘案流放夜郎,途中遇赦东归之时,那重重山岭间突然迎来的自由与生机,赋予了诗句飞扬的神采,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劫后余生的狂喜与对未来的憧憬,又如杜甫的《春望》,“国破山河在”的沉痛,根植于安史之乱中长安沦陷的特定历史,诗人将家国破碎的巨痛,凝练于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的意象中,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悲剧紧密交织,了解创作背景,便是在我们与古人之间,架起一座共情的桥梁。
诗歌的作者,是这文字阵法的构筑者,他们的性情、抱负与经历,决定了诗歌的气象,读苏轼的《定风波》,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,这份旷达与从容,非经“乌台诗案”的生死淬炼而不能得,我们在他笔下,看到的是一个将满腹苦水酿成诗意甘泉的智者,而李清照的词,从早期“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娇憨清丽,到南渡后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的悲凉沉郁,其个人命运的剧变,在词句中刻下了清晰的年轮,读懂作者,便是握住了开启诗心的钥匙。
至于诗歌的使用手法,则是其魅力的核心所在,赋、比、兴,如同三种基本的色彩,调和出万千诗意世界。“赋”是直陈其事,如汉乐府《江南》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,铺陈出一派生动的劳动场景。“比”是借此言彼,贺知章《咏柳》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将无形的春风化为有形的剪刀,巧思妙喻,顿生趣味。“兴”则由物起情,《关雎》以水鸟和鸣引出君子对淑女的思慕,情感的发生自然而然。
更进一步的,是意象的营造与意境的构筑,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,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一系列意象的密集铺排,无需任何赘言,一幅苍凉萧瑟的秋日羁旅图便跃然纸上,孤寂愁思弥漫其间,意境由此而生,它是读者凭借意象引导,进入的那个可供心神游弋的审美空间。
在今日,我们应如何与诗歌相处?它绝非书斋中的标本,而是可以“活”在当下的生命力。
其一,将诗歌融入日常表达,未必需要出口成章,但在特定的情境下,一句恰到好处的诗词,胜过千言万语,登临山顶,或许会自然涌起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;月夜独坐,可能更能体会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的况味,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表达复杂精微情感的最凝练语汇。
其二,以诗歌滋养内心秩序,在信息喧嚣、节奏匆促的时代,诗歌是一方宁静的后花园,王维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教导我们在困境中转换视角,获得心灵的安顿,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展现了一种与自然合一、远离尘嚣的生活美学,读这样的诗,是在进行一种精神的“呼吸吐纳”。
其三,借诗歌创造生活意趣,可以尝试组织家庭的“飞花令”游戏,或在旅行时循着古诗词的足迹,进行一场“寻诗之旅”,站在黄鹤楼头,吟咏崔颢的诗句;漫步西湖苏堤,体味苏轼的意境,诗歌便从纸面立体起来,成为连接古今的鲜活体验。
又遇见诗歌,是偶然,也是必然,它沉淀了千年的悲欢离合、智慧哲思,静候着每一次心灵的叩问,不必将它奉上神坛顶礼膜拜,而是视作一位渊博而温和的友人,在某个微风拂面的午后,或是一盏孤灯相伴的深夜,随手翻开一页,让那些历经时光洗礼的文字,悄然照亮我们当下的生活,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,正是诗歌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